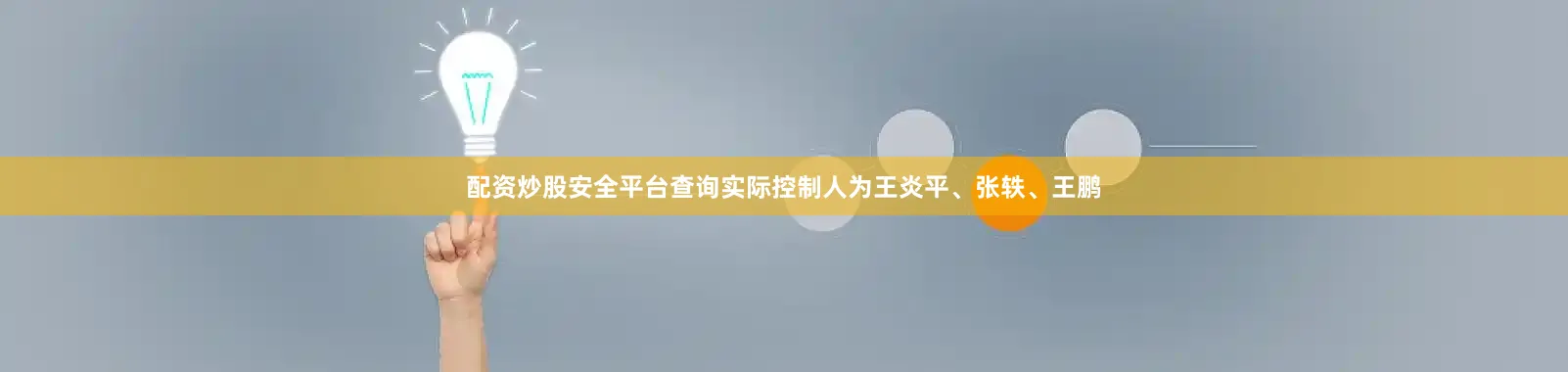一扇开合间,可观四时流转、笔墨精神,亦能感触地域文脉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“咫尺乾坤——馆藏明清山水画扇面展”以76件馆藏珍品为载体,以明清山水画扇面为切入点,不仅梳理了扇面艺术从实用到审美的演变轨迹,更通过地域画家作品的呈现,构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文化表达。当观众在盈尺方寸中读懂“天人合一”的哲思,文物的传承价值便得以真正实现。
扇子最初是应对暑热的“摇风”“凉友”,是华夏先民顺应自然的智慧之器。在演进的过程中,它在实用功能之外,融入文学与艺术内涵,形成独具特色的魅力。
汉代是扇子普及的关键时期,上至皇室仪驾的障日蔽尘之具,下至民间引风招凉之物,扇子的使用范围贯穿社会各阶层。此时的扇子逐渐脱离礼制束缚,向实用化发展,制作也日趋考究——材料除竹、羽之外,又增加了缯、绢、罗丝织等织物,为后来书画入扇埋下伏笔。宋代以后,折扇开始流行,到明清时期已成为主流,其形制之巧、材质之丰、书画之精,将实用与审美推向极致。
展开剩余76%秋到江楼图扇页(国画) 明 朱士瑛
从种类上看,中国扇子早已形成丰富体系:竹扇、篾丝扇、玉版扇、羽扇等因材质得名,团扇、折叠扇等因形制区分,纨扇、罗扇等则因扇面材料归类。其柄或竹或木、或骨或牙,其扇面或纸或绢、或蒲或草,其工艺或编或织、或雕或画——中国工匠的智慧与文人的才华,都在这小小的器物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。也正因如此,扇子不仅成为“游走的艺术”,更成为古董收藏家争相追逐的对象。而文人墨客以丹青入扇的实践,更让方寸之间的扇面兼具纳凉消暑与寄情抒怀的双重价值,最终成为怀袖中的“咫尺乾坤”。
折扇的扇面常见的材料是纸,按颜色分为白纸素面和色面,色面中又分泥金、洒金、瓷青、黑色等;以质地来分则有绢本和夹纱。扇面纸色的流行可区分时代,一般来讲,金面明代居多,素面清代较为流行。这种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载体,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,虽常被人们称之“小品画”,却能容纳世间百态,在中国绘画史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明永乐后折扇绘画艺术达至鼎盛,明末清初尤为兴盛。团扇绘画曾一度式微,实物也逐渐稀少,至清代中晚期才重又兴起,与折扇绘画并行,共同成为文人雅士诗文酬答的重要载体,留下诸多传世名作。
明清山水画扇面中,水榭亭台依水而筑、村舍楼阁错落有致、峰峦叠石相间。这些景致在扇面这一盈尺天地间巧妙铺展,既让观者直观感悟自然山水的灵秀美好,又能细细品味传统绘画的笔墨韵味与构图巧思。同时,扇面中独具风貌的景致呈现,也将不同地域的山水文化特色静静彰显。
山水扇面从来不是简单的写景,而是文人精神的“镜像”。明清文人在扇面上通过不同季节题材的创作,展现其对自然时序的观察。他们以山水绘四时景致,既展现自然轮回与隐逸情怀的对话,呈现游弋、消暑、读书、观山等情怀,又让人于“自然—画面,画面—自然”的呼应中感悟“可行可望、可游可居”的传统审美,在“春山如笑”到“冬山如睡”的变化中感受文人丰富的精神世界。
松荫话旧图扇页(国画) 清 张崟
这一点在具体作品中有着生动体现:春游踏青、曲水流觞等活动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的文化活动,同时也成为扇面的主题,如明蓝瑛《摹黄鹤山樵山水图》扇页、清张崟《松荫话旧图》扇页等。夏山苍翠、吟诗作画成为文人消夏活动,如清恽寿平《梧桐庭院图》扇页等。
仿赵大年山水图扇页(国画) 清 高简
扇面虽小,却是明清画派风格的“显微镜”。明清画派的笔墨脉络从吴门画派的“清润典雅”、“四王”摹古求变的严谨法度,金陵画派的“苍润秀逸”,到岭南画家融合中西的灵动笔触……在咫尺扇面中,看见传承与创新,清晰呈现了不同流派的艺术主张:在素宣纸与泥金笺的材质差异中,将“笔墨即性情”的文人理念具象化,让观众直观理解技法背后的精神内核,代表性作品如清《樊圻水阁归舟图》扇页、高简《仿赵大年山水图》扇页等。
在众多明清扇面中,广西清代画家罗辰、李吉寿、谢元麒等,以独秀峰、山城、广西山水等地域景致为题材,在传统山水“灵秀”的基础上,融入地域风土的“清旷”——如谢元麒笔下的独秀峰,既遵循山石皴法的传统规范,又以简笔勾勒桂林喀斯特地貌的独特轮廓。这些作品以传统绘画技法为基础,凭借写实风格突出广西绘画特色,成为本土文化与主流艺术对话的见证。
2025年8月3日《中国文化报》
第4版刊发特别报道
《咫尺藏乾坤》
↓ ↓ ↓ ↓ ↓ ↓ ↓ ↓ ↓
发布于:北京市京海配资-股票杠杆开户平台-香港配资公司-辽宁股票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